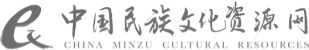女真与汉族关系
女真与汉民族的关系,同样要划分阶段来讲。宋辽金时期,在女真尚未建立政权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就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辽东一代的熟女真与山东半岛汉人的民间往来更为频繁,经常通过渤海湾出卖马匹。在金、宋对峙的一百多年里,尽管双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打仗,其他时间仍未中断经济和文化交流,双方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同时走私贸易也一度兴盛,成为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一个重要途径。
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初,阿骨打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场,以通贸易。宋即答书“并如来说所谕”。由于金灭辽后又发动对宋的进攻,设置之议未能实行。“绍兴和议”后的绍兴七年,金与宋协议在沿边设置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颖、蔡、巩、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设立榷场,宋置榷场于盱眙、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外,其余均关闭;宋亦只留盱眙一处,其余均关闭。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榷场亦关闭。“隆兴和议”后,金恢复榷场,宋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陕西沿边榷场只留一处,其余均关闭。开禧元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日多,榷场亦废置无常。宋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步、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花等。金宋榷场岁获税收反映出榷场贸易量颇大,如金泗州场,金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1196年)增至10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了近4倍。
民间走私贩卖量也很大。金、宋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时战事和,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商人为逃避税收获利,在榷场贸易中亦偷运私相贩卖。于是民间走私贩卖成了二者互通有无的另一渠道。据分析,走私贩易货物无论种类还是数量的,都多于榷场。宋臣在谈及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为例,说“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金朝私贩出境的主要是盐、米面、马等,宋朝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金境内的女真与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广泛而频繁的交换。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发挥了经济交流的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同时,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人士与官吏获得;二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女真文化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助益。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等,大多是由汉人参考了女真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写成。
金、宋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双方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宋朝方面,以西瓜为例,洪皓返回南宋时,将女真西瓜的种子带到他的故乡今江西鄱阳县,西瓜遂在南方普遍栽种。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表现在:女真人学习汉语,用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造女真文字;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其道可遵;金世宗命女真人知礼仪道德;今黑龙江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亦呈多样性:如南宋都城临安早在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已是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诸军又有效习蕃装,音乐杂以女真因素等。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河南开封)里,女真衣冠流行时尚,范成大《相国寺》诗中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明朝时期,明廷在东北一带设立都司对女真族进行管辖,并任命女真首领为指挥等大小官员,管理本民族。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进行。
到清朝时期,女真改名满族。与汉人的关系在清朝前期相对紧张,清朝统治者通过剃发、文字狱等统治汉族,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矛盾才逐渐缓和。
参考资料:李鸿宾等:《中国长城志》·《环境·经济·民族》,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