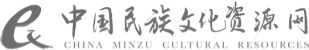草原神韵马头琴
马头琴是蒙古民族最具特色的擦弦类弦鸣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又名“胡兀儿”“胡琴”“马尾胡琴”等。蒙古语称作“莫日恩胡兀尔”,早期也曾叫做“朝尔”)。马头琴由共鸣箱、琴头、琴杆、弦轴、琴马、琴弦和琴弓等部分组成。共鸣箱多为梯形,个别为长方或多角形;箱框板用硬质木板制作,两面蒙以马皮或牛羊皮,也有正面蒙皮、背面蒙以薄板者;琴杆多用色木、梨木或红木制作,上部左右各有一个弦轴,顶端为琴头;琴弓多用藤条与马尾做成;两条琴弦分别用40来根马尾(里弦)和60根来马尾(外弦)合成,两端用丝弦结牢,系于琴上。

蒙古人爱马,对马头琴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关于马头琴的来源,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很久以前,在察哈尔(一说科尔沁)草原上,有一个蒙古族青年叫苏和。苏和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靠放羊过活。一天,苏和在牧归的路上捡到了一匹小白马,便将其抱回家中。在他精心照料下,小白马一天天变得英俊又健壮起来。它的嘶鸣像银铃一样清脆悦耳。一年春天,王爷举行赛马大会,并许诺谁取得冠军便把女儿嫁给谁。于是,苏和在朋友们鼓动下,骑着自己心爱的白马参加了比赛,一举夺得冠军。可王爷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还抢走了白马。白马日夜思念着主人。一天,王爷骑白马正在亲友面前炫耀,不料被马摔得头破血流。白马挣脱了缰绳,却不幸中了王爷的毒箭,待跑回主人身边后,终因伤势过重而长眠在苏和的蒙古包前。苏和失去心爱的白马悲痛欲绝,几天几夜都难以入睡,白马它那动人的嘶鸣总还在耳边回响……苏和为了纪念心爱的白马,就用其腿骨做琴杆,用头骨做琴箱,以马皮蒙琴面,用马尾搓成琴弦,拿套马杆做弓,并照白马模样雕刻了一个马头,制成草原上的第一支马头琴。从此,马头琴便传遍了辽阔的蒙古高原。
其实,作为马头琴前身的“胡琴”(汉籍也写作“胡兀儿”。蒙古语称“朝尔”),在蒙古汗国成立以前就已在蒙古民间广为流传。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把胡琴带到了欧洲,对西洋拉弦乐器的发展曾起到促进作用。《清史稿》载:“胡琴,刳桐为质,二弦,龙首,方柄。槽椭而下锐,冒以革。槽外设木如簪头以扣弦,龙首下为山口,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胡琴原型基础上,出现了长琴杆插入倒梯形琴箱、双面蒙皮、马尾弦和马尾弓的蒙古族拉弦乐器——“朝尔”。又经百余年流传,至民国初年,蒙古民间艺人将朝尔的头饰改为马头、琴箱变为上窄下宽的正梯形。
新时期以来,在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和内蒙古乐器制作大师张纯华等人牵引之下,传统马头琴形制不断趋于完善。共鸣箱得以扩大,改用蟒皮蒙面,拉弓弹性增强,用尼龙弦代替马尾弦,并将定弦提高4度等,使马头琴造型更加完美,音量和音域得到显著扩大,还推出马头琴家族新系列(如中马头琴、大马头琴和低音马头琴等),不仅可满足不同场合与不同形式演出,还可以拨弦弹奏。
演奏马头琴时,通常采取坐姿,将琴箱夹于两腿中间,琴杆偏向左侧。左手虎口稍张开,拇指微扶琴杆。在低把位上,用食指和中指指甲顶弦,无名指按弦,小指指尖顶弦,小指在演奏中非常重要,它常从外弦下面伸进去顶里弦;在高把位上,由于音位距离很小,各指都以指尖按弦。右手执弓时,以虎口夹住弓柄,食指、中指放在弓杆上,无名指和小指控制弓毛。运弓中,弓毛和琴弦要保持直角状态。马头琴的定弦有多种,因较细的弦在里,较粗的弦在外,所以常以反四度关系定弦为a、e,有时也以正四度关系定弦为A、d,正五度关系定弦为d、a。拉奏方法也与诸多拉弦乐器不同,琴弓的弓毛不夹在里、外弦之间,而是在两弦外面擦奏。右手弓法有长弓、半弓、短弓、跳弓、连弓、连跳弓、顿弓、打弓、击弓、碎弓和抖弓等,左手指法有弹音、挑音、颤音、打音、滑音、双音、拨弦、揉弦和泛音等技巧,许多装饰音都由小指奏出。就这样,看似构造简单的乐器,竟能演奏出如此恢弘深沉、悠扬醇美的天地和声!
马头琴天赋草原神韵。
现当代杰出的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主要有色拉西、巴拉干、桑都仍、齐·宝力高、李波、达日玛、巴依尔、张全胜(布仁特古斯)、朝克吉勒图以及颇具忧郁气质的马头琴手哈日布赫等。马头琴名曲主要有齐·宝力高《万马奔腾》、臧青诺日布《圣山》、辛沪光《草原音诗》等。近年来,随着马头琴蜚声世界音乐殿堂,新作不断涌现。

图为马头琴大师李波等在演出 乌恩特摄影
2006年5月,蒙古民族马头琴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马头琴文化传承保护基地”,鄂尔多斯乌审旗建有中国马头琴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