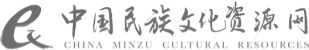古藏文
藏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文臣吐米桑布札赴天竺学习,参照梵文,结合藏语的实际情况创制而成的文字,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它虽然经历了改革和规范化,但基本特点未变。藏文30个字母都与元音a相结合,其他元音另有符号表示。30个字母本身都可以是独立的音节,而且有的字母就是有意义的单位——单音节词。尽管如此,字母的主要作用还是用来表达辅音音素,当它们与其他元音拼合时,附着在字母上的元音a被其他元音取代。可以说,藏文是一种音节-音素文字。
藏文的拼合方法分为基字和加字(前加、上加、下加、后加和再后加)的组合,再加上元音符号,构成音节,音节单独或连缀而成词。
从历史上看,藏文文献可分五个时期:一、上古时期:指公元6世纪以前,时间很长,文献绝少,只能靠后人的推断与构拟。二、中古时期:指公元7世纪到9世纪末的300年,或称吐蕃时期,留下文献不少,并有专门研究的论著。三、近古时期:指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约300年,各地豪强割据称雄,教派林立,伪书纷纷出世,学术思想颇为活跃,学者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四、近代时期:指13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末,政教合一政体形成,与内地关系密切,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哲学、史学、文学著述很多。印刷术传入,文化事业发展。五、现代时期:指20世纪以来,语文、文化、教育、出版各项事业都有长足进步。
吐蕃时期的文献除了翻译的佛教经典以外,目前得到确认的有三类:
第一类:藏文手卷写本。大部分出自敦煌石窟,一小部分出土于新疆婼羌米兰故城旧堡。总数约在5000卷左右。流落海外的分别收藏在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和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国内有一部分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县文化馆内。
在英国的藏文文献,由比利时人威利布散(1869-1938)编成目录,1962年出版。名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古藏文写本目录 附:榎一雄汉文目录》。
在法国的部分,由拉鲁女士(1890-1969)编成三册目录,分别在1939、1950和1961年出版。名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搜集的敦煌古藏文写本清册》。
此外,列宁格勒也藏有古藏文卷子。
藏文写卷的译解、研究有很大进展。20世纪20年代有B.劳费尔以P.T.3550号卷子为基础写出一著名论文《吐蕃的鸟卜——对Pelliot3 530号卷子的诠释及9世纪藏语语音学研究》,对学术界产生极大的推动。
20世纪30年代有托玛斯利用敦煌藏文卷子写出《论沙州》、《论和阗》、《罗布泊地区》、《突厥考》、《吐蕃的军队》等系列论文,最后汇成一本《关于新疆的古藏文文献集》Ⅱ。此外,还有巴高,拉鲁参加到这个行列。20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成就是巴高与托玛斯、杜散三人通力合作对P.T.1286、1287、1288、1247诸号卷子译解编著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关于这几个卷号藏文研究工作不断深入,麦克唐纳夫人、张琨、佐藤长、山口瑞凤及王尧都有新的论著进行讨论。
此外,关于P.T. 1283号卷子《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叙》是描写、记录突厥及其他北方民族情况的实地调查报告,引起了藏学界、中亚学界广泛的兴趣,先后有巴高、克洛松、聪果尔、韩伯诗、李盖提、森安孝夫和王尧著文讨论。
P.T.986号《尚书》藏译文残卷和P.T.1291号《战国策》(或指为《春秋后语》)、藏译文残卷的还译、诠释是近十几年中的新成就。同时,还有P.T.992,P.T.1284和S.T.M5、724号三个卷号都是《孔子项托相问书》的藏译文。也是在近十年中取得的新收获。
第二类:金石铭刻。这是古藏文中最能反映时代面貌的文献。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一共发现并经过研讨得到承认的大致有13件,分别是: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石刻、谐拉康碑甲、谐拉康碑乙、谐拉康刻石、赤德松赞墓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楚布江浦建寺碑、桑耶寺钟、昌珠寺钟、叶尔巴寺钟。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又有新的发现:
一、洛札摩崖石刻:在西藏山南洛札县城东洛札其曲河与门当河汇流之处的石壁之上。同一内容又有一处在洛札县城西北五公里的多穷村右侧石崖上。有藏文150多个。见巴桑旺堆文。
二、热扎寺碑:在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东嘎区尼达公社瑶地方的热扎寺旁,正面刻藏文39行。见仁欧罗桑文。
三、不丹廷布钟:为8世纪之遗物,上有藏文3行、环行、与昌珠、桑耶寺外大致相同。现存于不丹廷布的三宝寺。见于马可的《不丹——喜马拉雅山麓小王国的古代史》(1979年)。
另外,在四川西昌地区、宁夏银川地区也有零星的吐蕃时期刻石发现。
从事金石文字研究者有意大利人杜奇、英国人瑞查逊和李方桂、日人佐藤长等。
第三类:吐蕃简牍。绝大部分出土于婼羌县米兰的吐蕃军事古堡遗址,斯坦因、科兹洛夫各有所得,分别藏于伦敦及列宁格勒。1959年以后,特别是1973年,中国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又组织科学发掘,获得大量古藏文简牍。这一类文献所反映的语言、文字、历史、经济、社会、军事等情况与上述两类文献正可相互补充,相互发明。托玛斯曾译解伦敦所藏,载于他的专著《关于新疆的古藏文文献集》中。王尧、陈践汇辑《吐蕃简牍综录》一书,共收464支。
以上的三大类文献代表了吐蕃时期古藏文的绝大部分,它们的时代特点相当一致。
古藏文的主要特点:
一、从文字形式上看:1、保持元音i的反写形式,它的发音至今不清楚。2、保持了再后加字母da,即所谓强音da,俗称da-drag。3、单音字母不能自成音节,必须加上va,叫做单字母垫音。4、在复辅音群中,或者在同一个词的第二个音节中,清音的吐气与不吐气经常互换,不影响其意义,可能反映了当时实际语音。5、m作为辅音与高元音i、e拼合时,颚化现象(即mi >myi; me >mye)比较明显,与今安多方言一致。6、后加辅音da与na,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7、前加辅音ra与da,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8、若干正字法例字与现代不同。9、有大量缩体字(如: mthong-khyab,通颊,缩成为mthyong等)是约定俗成的简化趋势。10、隔音符号用[:]与今天[.]不同。
二、从文章风格上看:
1、一般不用长句,短小精炼。2、绝少使用藻饰语词,开门见山,朴素无华。3、敬语已在使用,对于国君、大臣、长上及佛、菩萨等已有专用的敬称语词。4、诗歌采自天籁,比兴手法,排比偶句。5、绝少署作家名。
三、从思想和精神状态上看:
1、对原始的自然神灵崇拜气味甚浓,人与神之间的界限不大严格。2、佛教的基本思想并未占统治地位,在文献中可看出斗争的起伏。3、阶级观念逐渐形成并明朗化,从誓约、盟词中看出其社会阶级的分解。

藏文《大乘无量寿经》
编辑:王韵茹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