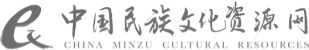乡村民俗与乡村景观的传承与演变 ——以江汉平原天沔地区乡村为例
内容摘要:
传统村落面临着村落景观演变退化和文化传统遗忘等问题,现代农村正不断失去乡愁记忆。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天沔地区传统民俗活动的传承延续与乡村空间的演变关系分析,强调了传统乡村民俗对于在当前的乡村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凝聚乡村社会关系,延续传统生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避免乡村被同质化甚至沦落为消极、失落空间的危机,同时营造积极的、多义的村落空间,赋予空间场所性与历史感。启示规划设计者应该重视传统民俗的生长保护,尊重乡村景观主体性,注重规划设计的人性化,从而引导与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
关键词:乡村民俗;乡土景观;村落空间;天沔地区
一、乡愁视域下的乡村民俗与乡村景观
今天,所谓的“景观”旅游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一种当地的古建筑、古街等景点,人们更希望看看当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也希望通过饮食、民俗等了解甚至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但可惜,这样的愿望常常落空,不仅闻名遐迩的古村古镇如丽江、乌镇的生活方式早已泯然于众,那些原住民将物业出租后搬迁到条件更好的城里,原有生活形态早已随之消失,其商业氛围堪比北京三里屯酒吧街,这样的传统村落即便有一些民俗展示,也只是布景一样的摆设,不再具备生活的本真气息。而在平常的普通村落里,民俗的保留似乎更多代表着某种落后,是现代化发展的反义词,也正普遍失去了自身特色。总之,古村原汁原味、“素面朝天”却难以与世人见面成为了一种当前乡村景观保护的悖论现象。
古村落古城镇和文物一样都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据统计,在我国230多万个村庄里,仍保有传统民居和民俗的古村落已不足3000座,而且随着商业开发和现代化浪潮的侵入,还在加速消失。但大量传统村落“空心化”,以及大量的建设性破坏却是传统民俗保护最大的威胁。这笔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今天的我们,更属于未来的子孙,绝不能为一时之利而随意开发破坏。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指出,民间的口头文学、民间记忆、乡规乡俗、地方精神这些扎根于村庄中无形的文化积淀了民族的精神、道德观,也保存了最深的地域多样性。如果没有这些村落,民族的特征也就消失了。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最终的问题还是要留得住人,如果没有人住,村规、民俗、村里的历史记忆就将消失,“乡愁”也就不复存在①。然而,新农村建设的观念误区是将城镇化异化为盖房子、拓道路,复制城市——推平了稻田,建起了宽阔的马路,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甚至农民们都上了楼。新的农村居民点,看起来房子更漂亮了,村容更整洁了,但却了无生气。一些“被上楼”的居民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房有了,地没了,生活方式不适应,社会存在感也没了,对未来感到无助与茫然。这样粗暴的城镇化,完全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形态,表面看起来富丽堂皇,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乡村生活的本质内涵。
二、江汉平原天沔乡村的研究

图1: 天沔地区典型的新房样式
本文讨论的湖北天门、沔阳(即今天的仙桃市)一带的乡村,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这一带平原辽阔 ,湖港交织,平川千里,河湖密布,自古素以“鱼米之乡”著称,也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然而在村庄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很多典型的问题。
1、乡村景观问题的提出
一是村庄空心问题。
农村青壮年人口缺失,农业适龄劳动人口短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外出务工,多数村庄的留守人员被称之为“386199”部队,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弱化、老化和女性化,也给农村正常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户整体搬迁到城市务工或居住,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尤为典型,造成了平日里村庄人气不足,萧条,这也带来了村落住房的空心化、人房分离问题。
天沔人勤劳能吃苦,很多人家在外省如广东、湖南等地常年做生意,然而,通常老一辈天沔乡村人外出打工创业赚钱后,则会首先选择在乡里盖房子,即使是倾其所有,也要盖上两、三层的楼房。即便是在城市购了房,多数也会保留农村的宅基地,有条件者也会新盖楼房,且投入不菲。然而,由于工作的重心已经远离乡村,乡村房屋季节性、长期性的闲置越来越普遍,通常只在过年时候集中使用。由于住房很多时间弃置不用,资源常常荒废,也导致住房仅成为村民外出创富的“符号”,如偏好使用大体量的欧式建筑装饰,楼房层高过大,屋内空间很不紧凑,耗钱较多却并不实用,甚至有些房屋基本朝向也没有先前讲究,出现大量节能很差、实际舒适度很低的“豪宅”。
二是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在江汉平原农村地区,尤其是城市郊区和工业厂矿附近的村庄,也遭受了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较差,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污染不够重视,再加上基层政府引导不力,既有农业生产性污染,也有日常生活性污染。在湖北天门地区农村,农村生活垃圾随处堆放现象尤为严重,尽管居住人口下降,但是旧时保护乡村土地与环境的生活习惯已经改变。各种新型垃圾填塞河道现象非常严重,旧时江汉平原湖港交织的水文景观受到严重影响。居民改善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当然需要重视,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模仿城市新型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如各种可供利用的生活垃圾不再收集处理,而是随意丢弃于屋后。如大量包装泡沫、塑料等,很难以被土壤降解,白色污染触目惊心,夏天则蚊蝇滋生,居住环境令人生厌。
三是文化生活贫乏问题。
村庄公共空间萎缩,村落的生活文化记忆迅速消失,公共文化活动缺乏。过去的集中性的娱乐方式逐渐退出现代生活,如今,大部分村民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打麻将、玩纸牌,公益性、全民性和健康性的村庄文化活动越来越少。年轻人则多去附近城市上网、游戏,村庄的人际关系也受其负面影响,那些传统盛行戏剧、曲艺等各种传统技艺等等,除了少数老龄人口,日益失去了传承人与广大受众群体。
有意思的是,当下关于村庄风貌的关心,乃至文脉、文化的问题,村民却并没有像专家学者这样,表现出关心,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更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如生计、务工、创业赚钱、娶妻生子。这些传统文化问题对他们而言显然还是奢饰品。另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者眼中,乡村民俗也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无论是管理者、设计者与村民对于农村建设的理解还是有很大误区的。而在设计师笔下,乡村风貌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木板、石头这些材料成为设计师的乡土符号,然而传统的乡村建筑形式与空间机理与当下的乡村生活已经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设计规划管控的意义大打折扣。更关键问题在于,乡村人对于乡村的归属感、记忆和情感也正在不平衡的城乡关系中不断稀释。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如果连乡村生活习惯、民俗文化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么重建乡村的物质性景观只能是沦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在这里,乡村民俗与乡村生活的延续与重建必须是也只能是乡村景观活力的唯一源泉。
2、乡俗传统延续与乡村景观重构的关系分析
(1)乡村婚俗中的人文景观与社会功能
在湖北天沔农村,由于大部分人口外出务工从商,春节作为家庭亲友团聚的节日功能显得非常重要。这一问题在这一地区农村表现非常明显,在这一时间里面,各种乡俗只能在这一时间段操办,仅仅是传统的婚丧嫁娶,如起屋、满月等。而错过这段时间则再找不到人来参加。由于在城市外出打工群体很多并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加上村俗与老辈人观念,大量外出务工青年仍然选择由乡里亲友介绍,回家进行频繁、高密度的相亲,一旦相中,则很快举办婚礼,婚后再共同谋划事业。找同乡人“先成家,后立业”也是一种适应当前城市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而婚俗的传统化则成为这个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天沔婚俗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婚嫁活动中举办的仪式、礼节、习俗活动、禁忌以及寓意的总称。主要内容有:婚前“发八”、“接八”(一种订婚仪式);送端阳茶、送中秋茶、男方报日、女方开单;迎亲前二天杀喜猪陪媒、过礼、前一天上头;婚嫁当天陪十弟兄、接亲、哭嫁、拦车马、牵亲、陪十姊妹、送亲、喝朋茶、穿厨、闹洞房;第二天早上端早茶;第三天新娘回门;以及过礼的礼物、新娘的嫁妆物品的规定等等。整个传统婚礼过程一般由咨宾(长辈)设计和安排。仪式感特别强,体现了避凶求吉、求全美满的强烈愿望。总体上来说是沿习先秦时代婚嫁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古习。

图示:1-准备上场的公公 2-叔字辈亲戚 3-背媳妇
现代乡村婚礼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例如纳入一些城市的、西化的婚礼内容,穿婚纱、拍婚纱照,尽管近年来举行婚礼的过程有所简化,婚礼越来越有西化的趋势,与传统相比虽然简化了很多,但是因为乡俗强大的影响力,且一般家里老人恪守,大致的传统礼节和程序都还在,总体而言,现代天沔婚俗和现在城市流行婚礼相比,仍然非常丰富,显得格外热闹。这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现代婚礼讲究效率、模式化、商业化、职业化的特点。而更多具有丰富细腻的地方文化色彩和大众参与的文化精神,人与人之间也有大量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例如,在天沔传统婚俗中,迎娶活动中的“公公背媳妇”这一节目颇为引人注目,按照民俗,包括“叔”字辈的亲戚都要轮流背新娘,这些背新娘的人称为“扒灰佬”,扒灰佬有“正宗”和“水货”之分。正宗是指新郎的父亲即公公,水货是指其他叔字辈的亲戚。因此迎亲阵容庞大壮观。凡背者均化妆,身穿戏剧服装,头戴各色衫帽,胸挂一朵大红花,五花八门,丑态百出,以此增添喜庆氛围,达到搞笑的效果,更成为一道街景。乡村人认为通过这一活动印证俗语;越闹越发。事实效果是,婚俗不仅增加了夫妻交流,也极大地融合了乡村大家族的情感认同,而其完全不同于城市里刻板单调的婚礼形式,亲友之间更藉此机会得到了很好地交流和融合的机会,由于现代乡村里参加婚礼的人们之间或者并不熟络,或因为平时都在城市打工,难以有见面的机会。通过这种大众参与、共同娱乐的过程,情感得到了非常顺畅、自然的巩固。血缘、地缘、族群等多层次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确定。这种强化对于现代常年外出务工、难以团聚的亲戚乡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避免长期距离疏远导致的关系离散化。
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乡俗传统与乡村空间的关系才显得更为有机,空间的表现上,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被凝聚,平时冷却的乡村街道被激活,例如传统的迎亲活动通常从村落的入口即开始,新娘下车,开始轮流背新娘活动,一直到自家门前,继而进门上楼。这个活动贯穿延伸于整个村庄的街道,乡亲街坊都会被吸引,人气十足。这一习俗的展开使之成为整个村子的喜庆事,平时人气不足的乡村空间也变得生机勃勃、活灵活现。
(2)蒸菜宴习俗中的时空景观生成
“蒸”是湖北菜常用的烹调方法之一,天沔地区被命名“中国蒸菜之乡”,在这里广泛流传的说法:"三蒸九扣十大碗,不是蒸笼不请客",蒸菜近年来已享誉大江南北,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好评。
首先,民以食为天,天沔地区蒸菜传统根深蒂固,渗透着天沔人的文化,这种深刻的味觉记忆,使得这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一方面培育了蒸菜的大量乡村厨师,也是一场大家庭充分筹划、动员、参与的活动。不仅要参与买菜、备料,在整个宴席的张罗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家庭、家族的的凝聚力。而为了满足这种制备过程,现在每家新盖的房屋一般都会保证一个较大的后院,包括土灶、柴火堆。而会留着一个侧门供小三轮车直通后院运货。
传统蒸菜的上菜特点是蒸笼高高地摞起来蒸,颇为壮观,一般多场宴席中吃蒸菜是正席,食物蒸好后,传菜的时刻具有极强的仪式感。例如按照习俗,正席上午那顿是不能超过中午十二点开席的。当亲友陆续到齐,列席入座,座次安排,事先交给老人处理,亲疏远近长幼尊卑的传统得以温习。随着开席的一声高喊,至少十几个蒸笼的热腾腾的蒸菜纷纷出笼,这时候满屋子甚至满街道的就成了雾气腾腾的景观。平日里没啥功能的高大宽敞的新堂屋在此时发挥了作用,而坐席现在则多是折叠的传统四方木桌,四个条凳,方便收取存放。一般坐八人,十个以上地方传统经典菜,其乐融融。当人数较多,门外边平时里看似空旷无用的平台、街道便可以充分利用成为街宴,冬天则可以支起棚架挡风,具有强烈的公共空间的意义。
现代各种庆贺宴席通常会请专门的班子搭置红色舞台,演奏喜庆音乐,并纳入新歌新舞蹈,接受点歌祝福,这一新习俗其实是传统搭台唱戏的一种演绎。在这一习俗中,整条街道也就不分彼此,成为邻里亲友共享的空间。宅前的街道成为活动的舞台,因此,各家各户宅前一般保持一个简单的平整宽敞的硬地,平日看来十分单调,而在节庆时候,如摆宴席、搭台子唱戏,门前硬地则不分彼此的使用,宛如一家。在天沔地区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风俗,但凡哪家有喜事,即便是不熟悉的乡邻,或有生意往来的人群如附近集市的流动小贩、小店家都可以送一个小小红包参与宴席,主人家也觉得很有面子,这种广泛的参与性以及大家轮流坐庄,使得宴席颇有点村庄公共食堂的味道,也非常有利于凝聚人际关系。

图示:1-后院厨房 2-街上的宴席 3、4 -开席传蒸菜
3、对乡村规划的启示
以往乡村景观研究中往往注意的空间形态,而乡村景观的时间性、时段性则是乡村建设中应该考虑的方面,在乡村空心化的背景下,乡村民俗将公共时间锁定,使得这一段时间发挥最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天门地区,一是过年时段,二是暑期,由于某些行业天热无法开工。因此,这一公共的时间成为人们回乡探亲聚会的机会,并与办理小孩升学宴、婚宴相结合。尤其是过年期间,各家会集中地办理各种宴会,除了婚丧嫁娶,新房上梁宴,落成宴,小孩满月、周岁宴等等,各种宴席上顿接着下顿,紧锣密鼓地进行,将这个年假日打造成了一个乡亲团聚交流的公共时间。这其中虽然有一些繁缛的礼节性往来,但对于久居外乡的天沔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乡愁情绪的一种表达,人们在这一时间并不是简单地聚会吃饭和应酬,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关系再造的情感物质交流。例如在外事业成功者往往积极参与各种人情世故,以此回馈乡亲,获得乡邻认同。而饭局的稠密往往可以带来交流的机会,在外务工者往往可以借此机会交流、共享信息,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由于血缘、亲缘、乡缘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宝贵。既是出门在外依靠的关系,也是情感交流的保证。乡村民俗的深入民心,老辈分人传承,即便是在外赚钱不多,也不能少礼数,要“保持”和“融入”这一文化圈,这既是根植于乡村人心理的深刻为人道理,也是在当下凝聚人缘关系,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精神追求。同时,以民俗凝聚了人心乡情,也唤起热爱家乡、回归家园的深刻情感。
乡村空间结构借助于开放的边界,在公私、内外、动静之间随机切换,形成了含糊多义的空间功能,如乡村的小街道,闲时扩展为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区域,赶集时是小摊贩、行商的据点,农忙时甚至变成晒谷子的场地。在本文的节庆婚俗中,又演绎成为凝聚社会关系与情感的舞台,因此,功能的多样化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与生产空间的交叠,这样的空间必须满足各种事件的发生、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又与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乡村记忆相联系,乡村习俗正是基于各种历史片段的堆叠而具有灵魂和各种新的个性,而我们对其空间的认知也要基于主体的记忆与主体的认同。
海德格尔就在思索场所与空间的关系时,深刻阐述了人在其中的意义,并把这种空间的终极理解指向人的“诗意栖居”,现实空间的意义更要基于它的人类学意义,是社会组织、社会演化、社会转型、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产物,其终极是一种人化空间,这些都启示规划设计者应该重视传统民俗的生长保护,尊重乡村景观主体性——村民, 尊重乡村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尤其要注重空间规划设计的人性化问题,注重空间规划、景观设计的大众认同,应注重引导与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才能健全、保护乡村的住居文化、民俗生活。
三、讨论与结论
“记得住乡愁”的乡村保护,有两方面内涵:从时间角度看,是要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实现与乡村原生环境的契合,避免大拆大建将乡村记忆拆除,保留地域的历史感;从空间角度讲,则意味着在人口自由迁徙和流动的基础上,通过新型城镇化弥合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让曾怀有乡愁的人能够就地择业发展,而不必远走他乡②。而在这一问题中,关键在于乡村如何留住人。简单让乡村增收,通过商业化、地产化的道路显然是片面的,也要靠乡愁文化情感来留住人心,唤起传统的记忆。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建设性破坏”都与地方错误的政绩观有直接关系,但这种以城市景观为唯一标杆的观念恐怕和缺少文化自信也有关系。正因为缺少自信,乡村古老陈旧的老屋,破败的老街古巷则毫不吝惜地拆回,而宁可拆旧建新。同时,正因为缺少文化的自信,而乡村人的精神关怀与文化传承也不被重视,导致这些珍贵的民俗日益消亡,乡村人逐渐趋向城市现代同质性的文化,而放弃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笔者相信,所谓景观的文化性与文化的景观化是一体两面,这其中都不能不重视村民这一主体性。
今天,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席卷,导致传统乡村地域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根植于地缘文化的乡土景观逐渐与日常生活想远离,如何进行在地性的空间重构与延续集体记忆,并与新的乡土生活、生产行为相联系,保护乡愁,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来源:《光明日报》传统村落保护:留住“活态”的村庄,2015年06月23日
②来源:《中国日报网》城镇化如何留住乡愁?止住乡村沦陷的步伐,2013年12月28日
参考资料:
1.李德复,陈金安.湖北民俗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王文斌. 译后记.后现代地理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