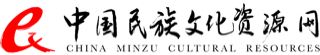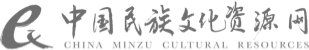契丹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契丹在立国过程中,征服了不少部族,诸如渤海、室韦、奚、乌古、敌烈、阻卜、斡朗改、辖戛斯等。但是纵观整个契丹发展史,与其关系较为紧密者当数女真和党项两个民族。
契丹与女真的关系:女真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在金建国以前,女真族主要受到契丹,也就是辽的统治。女真族同契丹的关系,呈现出时而缓和,时而冲突的特点。在契丹统治期间,女真族需要向契丹缴纳赋税,进贡物品,有时会因为契丹的过分剥削而奋起反抗。尤其是在契丹国末期,这种情况更加频繁,最终导致女真族中的生女真完颜部起来,攻灭辽朝。统治与被统治的角色进行了互换。
在辽朝统治期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女真各部力量发生变化,攻伐不已,为协调各部凝聚成为更大的集团成为趋势。石鲁任联盟长时,利用辽朝加授的惕隐官身份,讨伐不从者,扩大了联盟。乌古乃任联盟长后,女真以铁为兵器,继续扩大联盟,辽朝因授乌古乃“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到金穆宗时,终于使大联盟号令统一。至此,生女真绝大部分已纳入完颜氏控制之下的大联盟内。
生女真的日益强大,引起辽王朝的不安。辽朝从各个方面限制女真的发展,除了强征马匹外,还要求女真进贡北珠、人参、生金、麻布、松实、白附子、海东青等。在与女真人贸易中,经常强取豪夺,称为打女真。另外,契丹还派重兵防御,辽国皇帝也每年东巡。然而,辽国此时的统治阶级越来越腐朽,常为一己私利而破坏契丹与女真的关系。辽朝统治者每年派“银牌天使”到女真居住地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的名鹰,使者在女真地还要女真妇女陪伴,称为荐枕。为多得海东青,甚至发兵攻入女真境内。
女真各部终于忍无可忍,在首领完颜阿古打的带领下开始了反辽斗争。金收国元年,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在金军的打击下, 辽朝统治集团不断发生分裂,投降金朝的辽朝将领不在少数。天辅四年(1120年),金与宋签订了“海上之盟”,共同夹击辽朝。天会三年,辽天祚帝被金将俘获,宣告辽朝灭亡。在辽灭亡前,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已先前往伊犁河等地,随后建立西辽。尽管金朝一直想灭亡西辽,但终其一朝并未实现。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阿骨打于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诸部官民,投降的或者被俘的,不要以此为罪逮捕他们,以前是酋长的,仍给他们官,并找适宜地方供他们居住。这种宽容政策一直实行到天会十年耶律余睹叛乱为止。随后,金朝加强了对契丹人的控制。金朝让契丹人继续放牧,并且征收赋税,并要求契丹人无偿为女真贵族从事劳动。再来就是从契丹部族征兵,要服兵役。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反抗实行镇压和捕杀,同时也采用分散迁徙的办法防止他们谋变。这种压迫统治,最终引起了契丹人的反抗,直到金亡,契丹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
契丹与党项关系: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然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
辽夏交往的大部分时间处于联盟状态,是臣属关系。这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往来,特别是西夏位于东西交通的枢纽,两国的经济往来主要为朝贡贸易和中继贸易。
辽统和四年,西夏李继迁接受辽的封号,辽国成为西夏的宗主国。此后,西夏奉行纳贡义务,通过朝贡交换物品。辽国上京同文馆驿西南的临潢驿,成为接待西夏国使的专门地。重熙二年,辽国申令禁止夏国使沿途私自买卖金铁,反映了使节的经济交往职能。
中继贸易,是经过中间方或中介方而实现的甲乙两方的商品流通。西夏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间位置,这使西夏大获其利,甚至影响着辽朝与西域诸政权的贸易。如统和四年,李继迁叛宋附辽,随即辽朝与西方诸政权实现了每年一次的朝贡,夏国可以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引导西域贸易使团去辽或宋,西夏在其中进行转手买卖。
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与西夏在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也有往来,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商业条文,对西辽优待性的贸易政策,反映了西辽与西夏良好的经济交往。
契丹与其他民族关系:辽国幅员广大,不仅和宋朝汉人、西夏党项人经常来往,还和诸如高昌回鹘、河湟吐蕃等有密切关系。这些民族大多保持着和辽的朝贡友好往来。
回鹘早在唐朝就与契丹有联系,契丹曾为其臣属。契丹从立国到辽保大五年灭亡,回鹘一直保持着和辽的朝贡关系,成为辽的羁縻属国。回鹘和辽朝经济往来以朝贡贸易为主,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物品繁多,如珠、玉、乳香、琥珀、玛瑙器等,回鹘豆、西瓜、回鹘医药也传入辽国。西域的回鹘人常来辽境内行商,辽朝在上京南城南门东侧置“回鹘营”,供其商贩居住。还有一些回鹘人任职于辽朝,契丹后族述律氏也有回鹘血统,更加密切了两族人民的交往。
辽宋时期,河湟吐蕃以青唐城(今西宁市区)为中心,建立了唃厮啰政权。自辽圣宗起,河湟吐蕃向辽遣使一直没中断。辽国曾与河湟吐蕃和亲,促成其与西夏议和,双方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参考资料:
1.李鸿宾等:《中国长城志》·《环境·经济·民族》,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2.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