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堃(1901~1998),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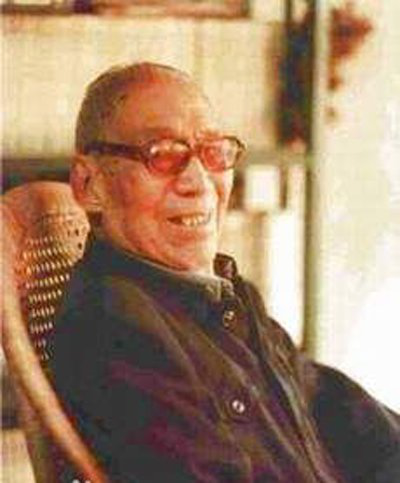
1928年杨堃赴巴黎大学进修,师从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随后又到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攻读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课程。同时,还在巴黎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听“原始宗教”的课程,又在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实习。1929年撰写《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同时撰写《法国社会学家访问记》。在法期间,杨堃曾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行,参观了几个较大的民族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博物馆,增强了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兴趣和信心,1930年夏杨堃回到里昂,获得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同时,与张若名女士结婚。
杨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民俗事象中的民间文艺现象的考察,而尤以对神话的研究为最突出。
首先是对神话产生与发展及其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的认识。对于神话的定义与范围,学术界多以马克思的定义为准。杨堃在《神话与民族学》等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神话的定义是从文艺的角度来下的,仅适合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他认为:“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群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仅能产生于五万年至一万年以前,即旧时期时代晚期,亦即 晚期智人时代。他以考古资料证明: 原始宗教与 原始艺术全产生于这个时期。由此出发,杨堃还对神话的发展、演变及消亡作了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晚期或石铜并用时期应是原始神话的发展期,这时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母权制向 父权制过渡。反映在 社会意识形态里,对当时神话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原始社会向 阶级社会的过渡期是原始神话的衰亡期,它开始向传说与史诗过渡。到阶级社会后,原始神话并未消失,一部分记于统治阶级的“圣经”之内,一部分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
对于神话的消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杨堃认为,任何民族,只要有宗教存在,就有神话存在,神话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 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与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任何时候,神话都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只要宗教存在一天,神话就存在一天,阶级和宗教消亡的日子,是神话消亡的日子,在神化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杨堃不完全同意 袁珂以“对待命运采取的态度”的区分法。他认为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尚未完全化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幻想征服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向大自然屈服,乞求大自然帮忙。这是原始神话产生的原因,也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而宗教与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分,相信宗教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则是迷信,因此,宗教与迷信同在,即使在 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依然存在。杨堃不同意民间文学界那种认为“宗教是消极的,神话则是劳动人民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的看法。
其次,杨堃还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研究民间文艺学及原始意识形态。杨堃学术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利用民俗资料,民间文艺资料研究民族学问题,同时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来开拓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角度与领域。在《女娲考》中说:“我发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仅知从民间文学的观点去调查传说,而不知从民族学的观点或民俗学的观点去调查这一民族、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与民间文化的全貌,那就带有局限性,而说服力不强。”1987年杨堃又写出了《图腾主义新探》一文,作为《女娲考》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认为彝族、佤族的葫芦崇拜、鸟图腾、虎图腾等都是母体崇拜,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在另一篇文章里,杨堃以“鲧腹禹”与“ 产翁制”材料,充分证明了民族学对神话学的贡献。他运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有关材料,证明“产翁制”产生的年代不可能太早,同时,又利用这些材料,去补充和分析了我国鲧禹神话的内容。在学术界,多认为“产翁制”发生于因 对偶婚制而产生父亲地位观念的 中石器时代。杨堃对这种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产翁制”的出现比对偶婚制的出现要晚得多,它之发生与对偶婚制之发生没有因果必然联系。“产翁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石铜并用期(亦即父权制初期)。这时,男子成为主要生产者,为产翁制这一上层建筑的产生打下了经济基础。为取代母亲在子女中的威望,男子便想方设法将生儿育女之功记在自己账上,这是“产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
除此,杨堃在民间文艺史探讨和国外民间文艺理论翻译介绍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可说是中国民间文艺的一篇简史,尽管其中观点不无商榷之外,但其史料价值是比较大的,有的甚至填补了民间文艺史的空白,如对抗战时期有关民俗活动的记载。翻译介绍方面,有《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令与歌谣》、《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派》等。在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民间文艺理论及国外学者对我国民间文艺研究状况,并借鉴其有益成分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